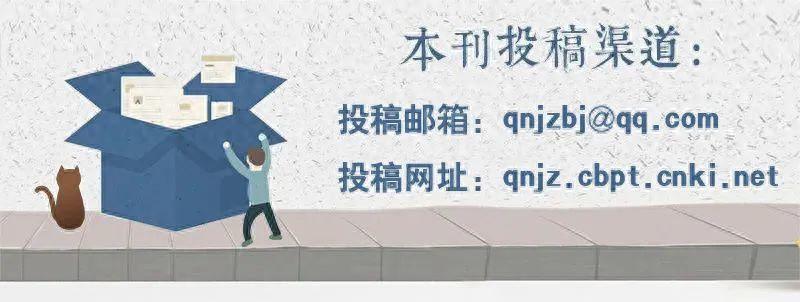
介绍:
本文以网络视频主播的身体遮盖为研究对象,从口罩遮盖和数字遮盖两个角度分析其内在的传播逻辑和文化意义。
1. 提出问题
近年来,网络视频行业呈现爆发式发展。 庞大的受众群体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视频内容的制作,网络视频主播也越来越多。 在视觉主导的消费逻辑下,“面子时尚”和“身体美学”塑造了当下接近“外表即正义”的“看脸时代”[1],造就了视觉优越的大众社会。 心理模型和行为习惯。 这自然促使网络视频主播通过美化、滤镜、P图甚至整容等方式修改自己在媒体平台上展示的“脸”和“身”,以获取观众的关注和消费。
有趣的是,在各种图像、视频展示和传播自我形象的网络新媒体平台上,一些网络视频主播选择掩盖自己的真实面孔和身体,以“脱体/面对”自己的形象。 出现。 没有了“外表”和“身材”,他们如何与观众形成新的社会关系? 不仅如此,数字虚拟技术的发展,对网络视频主播的身体遮盖行为进行了升级和改写。 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取代了真人的肉身,但部分获得了真人的“表情”。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基于此,本文确定了研究问题。 在这个不断追求真实的媒体世界里,网络视频主播刻意放弃视觉优势的身体感官和行为习惯,以物理或虚拟的刻意屏蔽行为面对粉丝和用户。 每个观众和主播都有一个隐藏的意义。 是什么样的心理动机? 主播与观众之间形成了怎样不同的社会关系? 虚拟形象与真人对话后,个体的内心身份和主观情感如何才能被悬浮? 本文暂时搁置主播的私密行为逻辑和心理机制以及资本驱动的消费逻辑,回到网络视频主播身体遮盖自身的现象来回答上述问题。
2. 掩蔽:自我重构与单向凝视
面部作为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身体其他部位不同。 是最直接暴露、展示在别人眼中的部分。 它以标志的形式描绘个人身份。 让-克洛德·施密特认为,无论是作为身份象征的脸、作为表达载体的脸、还是作为表征场所的脸,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人们认知历史的标签。的社会习俗。 [2] 面部遮挡是个体社会性的一种遮挡。 这也适用于互联网。 “不露脸”成为很多网民获得内心安全感、在非熟人之间传播信息的安全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与躲在“隐私暗室”的观众不同,网络视频主播通过主动曝光实现自我调解。 对他们来说,面孔既是表达自己并获得关注的一种手段。 工具。 当他们选择用各种面具、头套、娃娃服装、面具、墨镜遮住自己的脸时,传统的社会关系生成机制就被阻断,与以往不同的新型关系逐渐生成。
(1) 面具:身份面具与自我重构
打开任意一个短视频平台,美女帅哥霸屏。 我们甚至无法区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视频主播的面部差异。 在“脸盲”感的背后,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标准外表”构建了固定的“单一审美场”。 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视频主播通过化妆、美化来拉近这种“既定认知”,强化脸部本身的势能,从而吸引观众。 类似的审美机制,无形中对主播群体形成了一种互补的纪律形式。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差异化面孔已经成为主播被观众认可、记住和喜爱的基础。 另一方面,相似的形象也成为主播被观众认可、记住、喜爱的基础。 一种受受众调节、能够在互联网上获得关注的机制。 至此,面孔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视频主播进行视觉交流和建立关系的策略。 视频观众因脸认出主持人,因脸喜欢主持人。 在这种观看和接受被观看的互动中,面部成为两个社会团体之间的中介。
同时,面孔也是观众信任主播的基础。 主播获得关注的同时,他们原本的个人身份和社会经历也时常被网友曝光。 戈夫曼的戏剧主义理论认为,每个人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根据不同的场景(“前台”和“后台”)调整自己的行为。 [3]如果说网络平台的个人呈现是网络视频主播主动呈现的“前台”,那么“后台”则是被大多数主播隐藏或遮蔽的一种私人自我。 私人自我是一个安全的领域,“那些被极力压制的活动”“可能会损害它想要创造的印象”[4]。 然而,作为一个以博取关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主播,他的后台自我只能被“有限”地掩盖。 观众需要这个有限的真相来支撑他的台前表演,进而与主播形成认同。 这是一种无奈。 但一个有效的策略。 然而主播选择遮住脸,实际上以匿名的形式与观众形成了一种非常规的、半拒绝的互动。
面具实际上是对身份和个人社交性的掩盖。 主播不再是真实个体的媒介化,而是成为一种被媒介化的个体。 主播们用口罩遮住脸。 他们在获得身份安全感的同时,也放弃了以外表作为沟通策略、以真实身份获得认可的沟通渠道。 面具的遮盖,让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视频主播以悬浮的“媒体”形象出现在社交场景中。 粉丝观众自然无法通过视觉观看获得社交对象的身份表征,链接信任的协议也就终止了。 “眼见为实”或“透过管子看到”不足以让粉丝和观众从上帝的角度了解社会对象的完整身份和形象。 这必然会导致粉丝与网络视频主播之间的现实社会状况出现出入。 减少,观众不再基于现实世界的传播逻辑“信任”主播,而是形成新的认同。
由于这种真实身份的分离,戴着面具的真人网络视频主播有机会重建自己的身份。 不再有后台,前台可以彻底摆脱束缚,进入目的明确的新形象建构。 主播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设定进行策略性的设计,迎合和吸引观众。 没有了真实身份的束缚,重构后的身份更加纯粹、完美。 与此同时,主播和观众在一次短暂的见面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关系群体。 然而,这种群体关系并不是来自复杂的互动和长期经验的分享,而是一种“肤浅的、偶然的经验分享模式”。 用户在不同场景之间切换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交流。 相反,他们遵循了自己的沟通需求,陷入了表演舞台制造的幻象中。 [5]此外,面孔的缺席如同悬疑设定,吸引粉丝对面具下的真实面貌进行推断、猜测和幻想,从而构建粉丝的社会期待。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面具后的真人形成了美好的想象,用“神秘”的模式吸引观众。 2022年10月3日,一向以绿底白瘫脸(面具)形象出现、订阅量超3000万的国外游戏博主Dream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自己的脸部视频。 该视频发布后 12 小时内浏览量达 1800 万次,一周后浏览量接近 4000 万次。 然而,在一系列的赞美之后,Twitter上却开始出现对Dream外表的人身攻击和不断的辱骂。 或许正是这种无限想象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差距,才导致《Dream》受到诟病。
(2)沟通障碍:隐藏表情、单向目光
通过佩戴口罩,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视频主播与其社会身份分离,作为沟通中介的面部表情也被模糊化。 尽管网络社交媒体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并不相符,但表情作为个体情感的放大器,也成为主播实现情感沟通和社会关系构建的重要依据。 作为一种“现场”的身体反应,表情所承载的能指是无法被完全遮蔽、可以微妙感知的当下时刻,而所指对象则偏向于个体实时、同步的情感表征。 隐藏在屏幕后面的观众以凝视为手段,通过表情来理解和感知主播的情绪,进而实现对主播的制作内容和价值表达的认可、理解和亲近。 在观众的面部表情以及与直播网络视频主播的交流过程中,原本一对多的交流达到了“一对一”交流的假设。 原本对所有观众说的话,在个别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似性。 私人面对面社交互动的感觉。
当然,观众是清醒的,他们并不期望主播以独立的、私人定制的情绪来反思自己。 相反,他们以一种旁观者的目光形成情感感知和共鸣。 看不到观众的主播通过观看并接受评论/弹幕/礼物对虚拟观众形成情感反馈,从而形成近乎双向的观看。 这种“观看+社交”关系的生成是通过基于内容的表情/面孔来实现的。 当主播选择戴口罩时,双方的沟通心理发生变化,这段关系就被阻断了。
从主播层面来说,没有了眼睛的注视,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视频主播无法再向观众提供相应的面部表情和情绪反馈,从而从观众的视觉期待中解放出来。 换句话说,口罩对网络直播视频主播形成了情感上的保护。 除了声音和表情之外,主播无需关心自己在视频中的“情绪管理”。 无论是头饰、面具还是特殊面具,其实都是“固定”的表情图像。 原本丰富的个人情感被简化为不及物的“表象”,主播真实的个人自我很大。 学位模糊了。 在这个过程中,主播原有的个性和主观性本质上被弱化,形成了一个客观化的“物”,坦诚地接受观众的目光而不做出回应。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当被观看的物体以固定图像的形式呈现在他们的目光中时,本来可以持续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丰富情感信息就消失了,他们进入了一种观看。 图层的“失焦”状态。 这种失焦的观看方式也导致他们的情绪反馈失去了原来的焦点。 他们不能也不能指望主播会对他们的观看做出表情回应。 缺乏表达,大大降低了双方关系的基础,从而进入一种弱关系或者去关系的旁观状态。 观察变得更加纯粹,主客关系从传递关系转变为观看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双方解放的过程。 这种观看方式放松了社交互动中应有的表达和情感。 视觉传达的权利也是平衡的,不需要目光接触,形成平等的平衡。 、单向凝视、主客分离,或许正是在这种相对更加自主的社会关系中,蒙面主播的受众积累并没有减少。 “黑脸V”经常穿着黑色运动衫,戴着黑色面具。 作为一名技术主播,他几乎从不在短视频中发言。 这种拒绝交流、拒绝露面的行为不但没有降低他的人气,反而让他的人气更高了。 这种自我物化的过程吸引了更多粉丝关注他的视频内容和技术表达。 面具成为了他的特征,成为了阻挡深入交流的工具。 在这种表面的观看关系中,《黑脸V》完全成为了观看的对象。 而当掩蔽从面部蔓延到身体时,这种自我客体化就变得更加明显。
3. 数字化体现:想象中的沟通和社交真空
虚拟主播利用live2D、MMD、UNITY等软件制作2D、3D模型来打造虚拟角色。 后台配备真实配音演员,利用电子设备捕捉表情、神态和动作等,控制前台虚拟模型人物的动作,实现控制。 虚拟主播司机。 [6]在这个过程中,虚拟形象背后的真人,即“中间人”,是一个自我隐含的存在。 如果说面具是真实网络视频主播的物理身体遮盖,那么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对真人的完全隐藏也可以看作是真实网络视频主播利用数字皮肤进行自我屏蔽的过程,具有负面影响。对虚拟网络视频的影响 对主播的调查可以看作是对网络视频主播遮挡身体现象调查的延伸。 就像遮盖身体的面具一样,虚拟网络视频主播也隔离了主播“形象”背后的真实身份,并重构/虚拟出一个新的“形象”作为社交场景中的物理存在。 但与真实网络视频主播因口罩遮挡而导致脸部消失、视线被遮挡不同。 数字符号的编码技术模拟虚拟图像“人”的面部、眼神、表情和情感,从而构造出与真人相似的虚拟图像。 差异化新社交场景。 在这样的社交场景下,网络视频直播主播与虚拟形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格局,主播与观众之间形成了怎样的社交关系,值得分析。
(1) 虚拟面孔:表情回归与想象力交流
与完全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人不同,虚拟人是借助数字手段由真人驱动。 近年来,以“金橘2049”、“刘夜兮”为代表的虚拟网络视频主播,用数字“皮肤”和真人“灵魂”的模型与网友互动,收获了大量粉丝。 如果说面具的遮盖导致真实网络视频主播的脸和脸下的真实身份被隐藏,并根据设定展现出一个新的“自我”,那么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则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编码符号建立新的“形象”,与用户进行视觉交流和社交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图像代码并不是凭空构建的,而是源自对无数真实人物身体的捕捉和总结。 创作者在充分拥有完美的真人身体图像的基础上,利用技术手段对这些具身图像进行提取、概括和塑造,进而构造出近乎完美的数字图像。 虚拟图像更像是无数真人图像的索引。 作为一种构建的完美拟像,它是一门符合社会外观审美的技术学科,从而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和青睐。 [7]
从这个角度来看,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在其构建之初就具有明显的“他者”目光的客体化构建特征,并被生成为被观看的对象。 虽然幕后的“中间人”仍然负责虚拟网络视频主播“灵魂”的表现,但真人的数字化、完全隐藏的身体,实际上让虚拟网络视频主播陷入了悬浮的虚幻之中。空间,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被注视”。 如果说真正的网络视频主播通过摄像头与他人建立联系,并按照他人的要求进行表演,实际上将自己物化为一种商品或一种符号[8],那么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在构建之初,就是“物”或“物”。 “象征化”。 数字皮肤成为悬浮在“人”和观众之间的中介。 它是一种被操纵的“物理形式”,实现了与观众的联系。
这与“银碳银滩”等实体覆盖(娃娃服)的主播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所不同。 与物理手段的全身遮蔽行为不同,数字符号编码的虚拟网络视频主播是“人”的“复制品”,它复制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瞬间的脸庞和表情。反馈。 借用技术手段,将“背景中的人”真实的个体表情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数字人脸传递给观众,实现了表情的回归。 撅嘴、大笑、大笑、生气等表情,成为观众与“台下人”进行情感交流的媒介。 换句话说,与面具表情固化带来的社交隔离不同,虚拟网络视频主播的表情反馈实际上强化了社交属性,让观众与虚拟“物体”进行情感交流。 这是一种想象中的交往。
虚拟网络视频主播与观众的交流通常基于屏幕,两端的情感互动则基于网络连接进行。 此时,虚拟网络视频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准社交”,即想象中的人际关系。 [9]数字技术的“中间人”与前台虚拟图像的联系,就像皮影戏中“皮影”与幕布上“影子”的关系。 但与皮影不同的是,银幕上的影子可以与观众即时互动,具有完整的自然灵魂。 当“皮影”活起来时,使用者会产生超越经验的想象力。 “超现实并不客观存在,而是由人类主动再现或在头脑中想象。图像景观的超现实改变了我们感受和感知世界的方式。” [10]同样,虚拟在线视频主播利用这种超现实的身体形象呈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并进入观众的体验。 “想象”缝合了虚拟与现实的断裂,形成了不同的体验。 《金橘2049》刚上线时就以视频制作作为内容创作方式,但屡屡遭遇阻碍。 然而,当它转战直播领域后,却意外地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喜爱,上线首周就收获了15万粉丝。 [11]借助技术手段,《金橘2049》不仅可以快速切换、拥有各种新颖有趣的造型,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还可以选择通过直播与对方互动连脉之法。 讲笑话、讲笑话,输出与纯粹直播完全不同的有趣直播内容,得到了用户的呼应。
(2)维度变化:2.5维度与社会真空
以抖音平台上的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刘夜兮”为例。 作为拟人化的数字符号,它具有“人”的形象,具有人类的身体形状、面部和目光。 然而,拥有丰富网络经验的观众不会误认为是真人,拟人化并不是人。 无论创作者如何改进建模技术,数字人都是人的“模拟”而不是真人。 观众观看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并不是因为模拟的惊喜。 这是对“不真实”的好奇。 通过凝视,观众与“天语”、“金橘2049”等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即时互动,让观众暂时退出现实生活,进入想象中的虚拟世界。 这个虚拟世界既是虚拟网络视频主播“生存”、“存在”的二维场域,也是用户与其实时交流的伪真实空间。 它可以看作是一种介于二维空间和三维现实之间的空间。 2.5维世界之间。 在这个2.5维空间中,观众和主播在“眼见为实”的视觉交流和社交互动中,可以虚拟出真实的表情和情感表达,成为暂时的、去身份化的旁观者。 ,享受“虚拟替身”带来的自由、愉悦和富有想象力的补偿。
值得注意的是,观众在整个过程中也以虚拟方式与主播进行互动。 观众通过点赞、评论、虚拟礼物、连续视频等方式与主播进行社交互动。 主播这边,“中间人”也目睹了网络上已经嵌入的观众评论、点赞和虚拟礼物,心情也超然。 目睹他操纵的“皮影戏”获得观众“虚拟”的喜爱,那些还停留在现实时空的“中间人”也进入了社会真空。 在这个真空中,数字皮肤遇到了数字反馈(各种喜欢、评论和礼物)。 通过上述想象,双方缝合了虚拟与现实的断裂,想象的存在成为虚拟网络视频主播与观众构建“真空”社交情境的有力支撑。 至此,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不同于真人的关系。 原来以主播表演和观众反馈为中心的传播路径,转变为双向虚拟传播,以数字图像为中介,引导观众进入传播真空。 主播与观众通过“双向奔跑”的“社交想象”架起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在现实与虚拟相互融合时形成一个去除身体与现实的真空社交场景。
无论是虚拟网络视频主播“刘夜兮”还是“天宇天宇”,人物形象本身都脱离了现实领域,以虚拟、想象的形式存在于虚拟社交世界中。 当“刘夜兮”开始主动介入现实世界和实时,帮助剧中人解决现实问题时,原本分离的两个时空奇异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超越维度、超越的虚拟时空。现实的背后,隐藏在屏幕后面的“中间人”彼此并不见面,但在这个空间中实现了中介互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4。结论
“面具”的使用是对网络视频主播身体的掩盖和修辞,“数字虚拟图像”的介入是对网络视频主播身体的隐藏和替换。 无论是“面具”的遮盖和说辞,还是“数字虚拟形象”的隐藏和替换,都构建了一种不同于线下面对面、也不同于线上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和人际交往。 -面对。 人机通信和人机交互模型。 面具的屏蔽和数字虚拟图像的介入,让网络视频主播和粉丝观众实现了“符号在场”和“实体缺席”的同时存在。 两者都可以忽略生物社会面孔、身体和身份,更纯粹地利用虚拟的身体在场并沉浸在追求沉浸感的媒体世界中,创造出一个在时空结构中忽略真实身份的沟通负担并忽视的世界。视觉传达关系的不平衡。 同时,抛开了观众对主持人表情反馈的期待,形成了一个完整、中间的真空社交场景。 这种游戏化、轻松的社交模式为互联网上的社交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们有理由期待,现实世界逐渐嵌入网络世界后,一个可以悬浮社会注意力的新虚拟空间正在产生。
参考:
[1][2]詹迪. 论“面子时代”年轻人的审美缺失[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10):101-106。
[3]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自我呈现[M]. 黄爱华、冯刚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1-29。
[4] 董晨宇,丁怡然. 当戈夫曼遇见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现[J]. 新闻与写作,2018(01):56-62。
[5]刘杰,杜娟. 传播的无奈:社交直播幻境下的现实思考[J]. 青年记者,2022(01):49-51。
[6][7]严道成,张家明。 科技神话与虚拟与现实的嵌套:消费文化视角下的互联网虚拟主播[J]. 深圳社会科学,2022(06):147-157。
[8]杨周松. “网络名人文化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教育研究,2018(12):4。
[9] 吴金华. 虚拟偶像传播伦理的失范与重塑[J]. 青年记者,2023(12):110-112。
[10]让·鲍德里亚。 拟像与模拟[M]. 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4:40。





